摘要:不是不想停下来,是停不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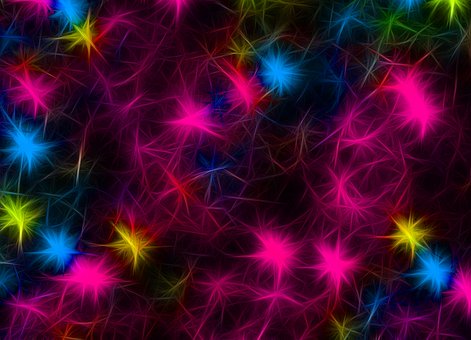
上周,高以翔在录制综艺节目《追我吧》时突然晕倒,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急救后离世,年仅35岁。该节目是深夜录制,且需要极大的体力消耗,这可能是引发悲剧的原因。
事件发生后,全网悲痛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娱乐行业过劳现象的反思和讨论。黄磊、袁弘、张雨绮等人在微博上发起了“12小时倡议书”,向全行业呼吁“工作不超过12小时,重返片场之间不少于12小时,两餐之间不超过6小时,拒绝疲劳工作”。
过劳的当然不止影视行业。今年三月,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在GitHub上迅速火爆并一路烧到了社交媒体。发起人写到:“什么是996.ICU?工作996,生病ICU。”
尽管缺乏对全面过劳状况的调查,但一项针对北京中关村和CBD企业员工的调研显示,61.6%的人已经进入了过劳死的“红灯预警期”,即具备过劳死的征兆,而处于过劳死“红灯”危险区的人,则高达26.7%。中国的过劳状况或已到达十分严峻的程度。
每当有因高强度工作而猝死的新闻出现时,总会引起类似“健康比工作更重要”的倡议和讨论。然而讨论过后,加班照旧。
这背后是我们的无奈:不是不想停下来,是停不下来。
1.奋斗是通往幸福和成功的必经之路吗?
还记得互联网巨头是如何回应关于“996”的抗议吗?
马云说:“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请问大家,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你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年轻人要明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刘强东则表示,京东人要有拼搏精神。
科比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马斯克每周工作一百小时;李佳琦一年直播389场……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足够努力,这样的奋斗叙事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甚至相信的。
这类叙事中似乎包含着某种对自主性的承诺,即个人是完全自由的,可以通过不断地奋斗去实现自己的人生计划和价值。
而与这种承诺对应的则是,如果你的生活陷入困境,那可能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对于是否足够努力的标准也一直在发生变化。艺术评论家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提到,技术瓦解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边界,“这个星球被重新想象成了一个永不停息的工作场所,或一个永不打烊的购物商场”。
“在全球化论者的新自由主义范式里,失败者才睡觉”。这个时代推崇的,是那些能持续在信息环境里参与、联络、回应或处理事情的人。永远在线成为了一种对于成功的必然要求。
2.我们必须越跑越快,才能够待在原地
对于有所渴望的人来说,不停歇地狂奔似乎是一种主动选择。但让更多人无法停下脚步的,是对于“不进则退”的焦虑和恐惧。
社会学者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竞争原则是界定现代性的核心原则。所有社会都需要找出正当的方式,来分配财富和资源。在前现代和非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分配模式,是由出身所预先决定。而在现代社会,则是竞争原则支配了生活中大多数领域的分配。
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我们所占据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永远的竞争和协商当中。在这种竞争逻辑下,人们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竞争力。
维持竞争力,不只是一种让人们能更自主地规划人生的手段,而是渐渐变成了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唯一目的。
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 在他的社会加速理论中解释了为什么科技的进步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闲暇,反而加剧了人们对时间匮乏的感受。
他认为,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加速变迁的竞争社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站在“滑坡”之上,技术、知识甚至生活方式,只要稍微喘口气,就马上会变得落后过时。任何以静止或变化慢为特征的社会现象都被边缘化了,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
“人们被逼迫着不断追赶他们在社会世界与科技世界当中所感受到的变迁速度,以免失去任何有潜在联系价值的可能性,并保持竞争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科技、信息乃至整个社会的不断加速反过来造成了人们生活步伐的加速。因为我们必须越跑越快,才能够待在原地。
3. 最自由的零件
罗萨在他的著作《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提出了这样的思考:一方面,现代社会要求分工合作,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当中的人又似乎是相当自由与自我的。没有人会规定要做什么、要信仰什么、要怎么思考……
我们怎么能前所未有地自由,却又前所未有地极度合作、协调、同步化呢?
他认为,有一种社会意识隐藏在主流的自由主义的自我感背后,以压倒性的力量实现这一切。在这种社会意识下,个体一方面觉得几乎完全自由,却同时感觉到被一长串清单式的社会要求所支配着。
回想一下,我们每天的生活是被各种“必须这样做”的事情所构筑起来的。这些事既是来自外界的要求,又是一种自我选择。“我现在真的得去工作了。我得去学个外语。我必须去看看这个新闻……”这串清单无穷无尽,到最后是,“我现在必须好好放松一下(以便可以更好地工作)”。
在一天结束之后,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有罪,因为我们没能完全完成要事清单。而且事实上,这个清单还会堆积得越来越多。
现代社会制造了这种“有罪的主体”。我们普遍认可的,是一旦我们无法实现社会的期待,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越来越多因为失业被排除在竞争之外的人们更是提醒了我们,这代价有多么高。
4. 我选择“不选择”
克拉里说:“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除了那些与个人占有、积累和权力相关的愿望,别的愿望通通被禁止。这些限制既是外部力量强加的,也是心甘情愿地自我施加的。”
在选择和自治的幻觉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在进行整齐划一的自我管控。
罗萨在他的书里提出了一种新的异化状态,不同于黑格尔或马克思,他将异化定义为“人们自愿做某些不是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的情况。
比如当我们加班到三更半夜,即便没有其他人规定要这样做,而且我们内心是“想要”早点回家的,那么这时我们就体会到异化了。或是当我们为了追逐更大的利益所以必须解雇某人时,也会有异化的感觉。
我们可能会对目标和做法感到怀疑,而且原则上我们也可以采取别种做法,但“我们还是得这么做”。
“当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时,我们早晚都会‘忘记了’我们‘真正的’目标和意图是什么,然后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们被他人管制了,但其实并没有外在的压迫者在管制我们。”
电影《猜火车》里主角出场时有一段著名的台词:“选择生命,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可恶的大彩电,选择洗衣机、汽车、雷射碟机,选择健康、低胆固醇和牙医保险,选择楼宇按揭,选择你的朋友,选择套装、便服和行李,选择分期付款和三件套西装,选择收看无聊的游戏节目,边看边吃零食......选择你的未来,选择生命……太多选择,你选择什么?”
“我选择不选择。”这是主角雷登的反抗方式。
可是寄希望于这种建立在“放弃竞争”前提下的反抗是行不通的。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我们之所以无法停下,是因为离开跑道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奇葩说在讨论“996”这个话题时,薛兆丰说了这样的话“让你996的不是你的老板,而是其他愿意996的人”。
所以我们要呼吁的,是能让竞争停下的制度性保障。欧洲提供了很多正面的例子。比如,为了道路安全和避免不当竞争,欧盟对客运货运驾驶员的工作时长做了规定,每日行车不得超过9小时,且行车四个半小时后至少需要休息45分钟,并通过检查行车记录仪来确保这些规定的严格实行。
西班牙自5月起实行了“工时登记法令”。法令要求所有企业雇员必须在上下班时签字或指纹打卡,用以确定工作时长。工会等机构会对记录随时进行查询和监督,一旦发现雇员真实的工时记录无法对应合同规定的工作时间,或雇主没有向雇员支付加班费,雇主将受到严格惩罚。
类似的法规和制度才能给我们以喘息的空间,让社会变得不那么像一个越滚越快的仓鼠笼。
相信会有人认为,欧洲和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如若每次类似问题的讨论都以这种无力的辩驳结尾,那我们需要承受的过劳与异化可能永远不会有改变。只有我们持续性地提出问题、引起公共讨论,才有可能真正推动改变的发生,就像开头提到的“12小时倡议书”或许就是一次开端。
我们是离不开这个竞赛场的,但希望我们跑向的,是真正的未来。